在剛剛過去的畢業季里,應屆生就業難仍然是個熱門話題。所以,當沒有實習經驗的西方哲學專業的應屆生陳安告訴我,他找到了一份月入過萬雙休不加班的工作,我有些驚訝。而且,他們宿舍三位西哲學專業的同學,都在卷生卷死的就業大潮中順利“上岸”了。
哲學上次引起社會的注意,大概還是農民工陳直“思考海德格爾”的事情,人們似乎覺得哲學發生在學術界才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。但如果說哲學是一門有著專業界限的學科,那些經過學院化訓練的人,會更不在意就業導向嗎?他們學到的知識和實際的工作又如何自洽?
600次投遞和一個offer
陳安拿到這個offer并不容易,他是一名上海雙非大學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。因為專業和學校的緣故,在最初找工作時就已經有了預期。他咨詢過學長學姐,對于哲學專業來講,大學教職、公務員、機構教師算是專業對口的工作。
但他首先排除了公務員等文職工作,“在我的想象里,這些工作有些無聊和重復,需要寫很多材料”;老師這個選項隨即也被排除掉,“雖然有寒暑假,但工作內容似乎一直在重復輸出,回顧過往的學習經歷,永遠無法逃出‘做題家’的魔咒。”
沒有實習經驗,沒有論文發表,沒有獎項且不是黨員,陳安在就業市場上被戲稱為“三無學生”。5月,臨近畢業時,申博失敗的陳安開始找工作,要求是:月薪8k以上,工作有發展空間,雙休不加班。留給他的選項并不太多,校招的激烈競爭中,他沒有優勢,于是轉投社招。

視覺中國 資料圖
學什么專業就要找什么工作,陳安覺得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了。但招聘軟件注冊后,跳出頁面需要填寫意向行業,他又有些困惑,不知道應該尋找怎樣的崗位。
“在學校里沒有接觸過社會中的各行各業,對工作的類型就缺乏想象。”不過,招聘軟件的算法幫了大忙,推薦頁不斷更新,從歷史文化研究員到科創領域的客戶運營,再到藝術展覽的商務策劃。陳安在招聘軟件上挑挑揀揀,投遞了六百多個崗位,有二十多家回復了他,其中有四家通知他去面試,最后有一家小型咨詢公司給他發了offer。
“運氣好”,他解釋道,這是一家不到十人的小公司,創始人從一家知名機構離職后自己創業,“老板希望找一些冷門專業的學生,因為我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咨詢,要和對方公司的管理層溝通,幫助他們進行管理系統的規劃,更看重的是邏輯思維能力和溝通能力。”
無用和有用
陳安宿舍里另外兩名西哲同學也沒有參加學校組織的校招,最終的就業選擇看起來也與專業本身無關。一名男生畢業后從事劇場的編舞工作,他本科就讀于舞蹈類院校,認為美學和哲學本身也是相通的,舞蹈可以是文本的再演繹,身體的運動和思維的運動可以融合在一起。
另外一名同學則去了跟教育有關的行業,負責教育產品和硬件的推廣,需要跟學校和家長進行溝通。此前,他也面試了一些教培機構,但直接講授課程更像是把自己作為商品售賣,既然所有崗位的本質都是銷售,不如做得更直接一些。一旦掌握了銷售的技巧,可以在很多工作崗位上用到。
在陳安看來,從專業學習的角度上來講,哲學常常要進行文本分析、研究概念、分析關系,比較鍛煉人的邏輯思維,這種做事的思路可以應用到工作中。哲學專業的同學會更容易理解抽象的事物,會把一件事情講得更加深刻,“有時候說一些術語,就很容易唬人,顯得思考了許多,因此在說服別人上有優勢”。
不過,目前的陳安,依然覺得自己還是哲學的初學者,總是處于輸入的過程之中,無論是一個人、一個概念,還是一種主義也好,都得把它放入具體的歷史之中進行研究。他也看不慣一些“灌水”的學術研究,“不少哲學生只是被動地拋進文本之中,寫出來的仍是陳詞濫調”。
但真正的哲學走得更遠一些,“讀海德格爾的農民工”陳直在陳安看來,就走得更遠、更真切一些,“陳嘉映鼓勵陳直要帶著自己的問題去研究,他說的問題不是今天早上吃什么這種具體問題,而是一種根本性的問題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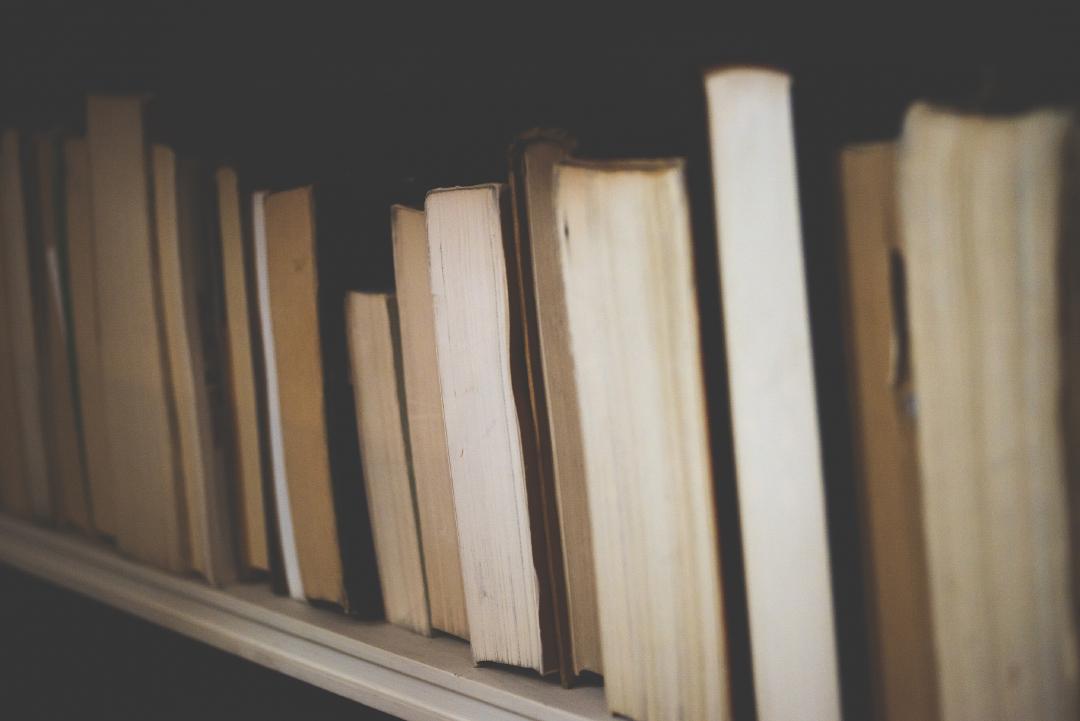
視覺中國 資料圖
什么才算是根本問題?陳安告訴我,有一本很火的書叫《毫無意義的工作》,里面描述到人做很多工作就像在做一顆螺絲釘,只是在運用同一套工具去處理問題,結束之后要前往下一個地方做類似的事情,就像站在河流里一樣,伸開手會發現到手心中空無一物。
如果把生活囫圇吞棗地過下去也還可以,但“一旦發現了生命有一個根本的問題需要去回答,就會意識到自己無法逃避”。因此陳安在找工作時,格外看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,在滿足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后,能有更多屬于自己的時間去學習和思考。
心靈的平靜
“哲學給我帶來了一些潤物細無聲的東西”,陳安說,“我對人的容忍度很高,因為我能夠很好地了解人與人之間的差異,以及他的一些思想背景,會更加平靜。康德就經常提到這件事情——人各安其位。”
這種平靜不僅是對人,對事也是如此。陳安在6月初時還沒有找到工作,但他沒有任何抱怨和焦慮,也不去對比別的同學找到了多么好的工作
我很好奇:哲學給人帶來平靜是通過什么途徑呢?
他告訴我:是通過一種思辨方式。“你會想有或者沒有工作,人總是有很多種方式能活得下去,對于沒有到來的事情不要抱有無限的恐懼。我們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來看待,時間就擺在那里,它就會讓你平靜。在人和事物在思維上產生一段差距時,焦慮會減弱。”
但回到具體的專業選擇上,陳安覺得文科類、社科類的專業其實差不太多,只不過有些更實踐化,比如說社會學的田野調查和新聞學的實務操作,歷史學的資料內容更多一點,而哲學更思辨,更抽象,更文本一些,在找工作時會被詬病“可用的技能和工具太少”。
他選擇哲學專業,也是因為偶然翻開了一本笛卡爾的《第一哲學沉思集》,“許多概念讓人耳目一新,幾十年前,哲學家已經揭示了現在年輕人會遇到的狀況,人們確實能發現一些自己的需要。”
現在,知識和文化資本被精英階層掌握,全民求知的時代一去不返,才會覺得哲學“遙不可及”,但陳安覺得:對生命的本質問題產生思考,不就是人的本能嗎?

